飛行資訊
販毒人生
快速導航
1.大不了幾歲的吳二叔
2009年大一寒假期間,母親讓我跟著姑婆去看看吳二叔。早上5點多,我和姑婆從寨子裏出發,歷經2個多小時的車程,終於來到了一座山腳下。
這是我頭一次近距離接觸監獄,看到一堵光滑的牆高聳著,牆頭還裝了密密麻麻的鐵絲網,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變得壓抑、沉重起來。監獄的會見室有點像銀行,一條長長的櫃檯把長方形的房間分割成兩半,上面是密封的玻璃牆,能看到裏面的人,但聽不到聲音,只能通過幾部電話交流。
會見時間到了,我們在指定的窗口等待。不多時,一道門打開,一名警官拿著紙開始點名,不一會兒身穿藍色囚服的吳二叔就跟在幾個人後面走出來,一臉的笑容。 幾年不見,吳二叔長胖了許多,皮膚也變白了,如果不是那副濃眉大眼,我幾乎都要認不出他了。
吳二叔只是輩分高,年紀其實比我大不了多少。我上學前班時,他讀五年級,每天都是他領著我去上學。學校在寨子對面的山腳下,沒有大路,得穿過一片田野。蜿蜒的田埂上有兩條水溝,一到下雨天,水很深很急,每次都是吳二叔先跳過去,伸手接我,我才敢跳。
吳二叔個子不高,很瘦,濃眉大眼,看起來憨愣憨愣的。但實際上,他在學校算個“小頭目”,下課經常帶著一幫高年級學生來我教室門口,“如果有人敢欺負你,就告訴我”。

可這種“保護”並沒有持續多久,1998年吳二叔小學畢業,由於學習成績差就不讀書了。我們寨子的四周被大山包圍,土地少,能種水稻的田更少,讀書是孩子們改變命運的主要出路。 但這條路很少有人走得完——要麼成績不好,升學無望;要麼家庭貧困,不得不早早輟學賺錢養家。
吳二叔家裏不指望他賺錢,只怕他四處遊蕩跟混混學壞了,就送他到城裏學汽修,做點正經 事。修車是個辛苦活兒,一鈷車底經常就是個把小時,又髒,一天下來滿身油污。吳二叔不在 乎,比起留在田地裏盤莊稼,這算是輕鬆的。
2年後,吳二叔進了市里的一家修理廠。實習期間,老闆供吃住給他30塊錢,後來逐漸漲到 300塊一個月。工資不高,但足夠養活他自己,曰子不好不壞,平平淡淡的。
可是到了2001年年初,吳二叔的命運被一個女人改變了。
2.介紹人
修理廠有個常客,是個30來歲的女人,總帶著夥伴過來修車洗車。她衣著時尚、穿金戴銀,腰 上還別著一部諾基亞手機——那時候,手機還是稀罕物,有錢人才用得起。一來二去,她就跟 修理廠的夥計們混熟了,她說自己姓郭,大家就都喊她“郭姐”。
一次,吳二叔正給郭姐洗車,她站在一旁說:“你在這裏修車有什麼前途? 一個月那麼點錢還 不夠花,不如跟姐做生意,吃香的喝辣的,什麼都有。”

吳二叔沒有答話,繼續洗車,郭姐看四周沒人,就伸出了一個巴掌:“幫老闆帶東西一次,起碼有這麼多錢。”
“500?”
郭姐笑了,說得再加一個0,“不然哪有那麼多人冒著槍斃的風險去搞這事”。
吳二叔當然知道郭姐說的這門“生意”是什麼。我們寨子靠近中緬邊境,十幾年前交通不便,出國比出省還快。從小我們就看到寨子裏很多人趁著農閒偷渡去緬北幹副業補貼家用——蓋房子、搞裝修、做餐飲、伐木……還有一些小青年不想老實幹活,賺點錢就在賭場裏賭,想靠運氣翻身。
緬北歷來不太平,又盛產罌粟,毒品氾濫。有些人偷渡過去不願意賣苦力,索性鋌而走險販毒,一趟下來,賺的錢抵一農民幹一年,甚至幹幾年;如果量大,拿到的錢是種一輩子地都賺不到的。
我們的寨子小,總共七八十戶人家,但被槍斃的人有四五個,坐牢的有七八個,當然,也有漏網之魚。吳二叔就認識一個,他穿好衣服、好鞋子,騎摩托載女友四處瀟灑,吳二叔十分眼紅。
不過販毒不是買菜那麼簡單,毒販往往都有組織,各環節分工明確,急蔽性強,外人想入行得有人引路。面對郭姐的邀約,吳二叔先是裝傻充愣,之後又忍不住問怎麼算錢?郭姐說,帶1克過來老闆給18塊,一次300到400克,“你自己算算”。
那時吳二叔年紀小,哪低擋得住這樣的誘惑,但他也知道害怕,並沒有立即答應。郭姐也不勉強,只是之後隔三差五就請他出去吃飯唱歌。
郭姐圏子裏的人都有錢,他們抽好煙,喝好酒,身上戴的非金即玉,很是風光。經過半年多的 “思想鬥爭”,再加上郭姐不厭其煩的遊說,吳二叔越來越覺得修車沒前途,便鬆口答應去幫帶一次。
吳二叔還記得,他第一次出發的時候正值盛夏,雨水充沛。他謊稱家裏有事,跟老闆請了一星期的假,然後踏了前往芒市的汽車。
除了吳二叔,郭姐此行還帶了兩個陌生的年輕人,聽口音也是本地的,打聽了才知道,他們和吳二叔一樣,老實幹活賺不到多少錢,可又想趁年輕過瀟灑快活曰子。
那時,去芒市還沒高速公路,只有一條滇緬公路可走。警方為了打擊販毒,在這條路上設了層層關卡,汽車在盤山公路上下顛簸,跨越怒江,翻過高黎貢山,窗外的風光驚險又美麗,可吳二叔無心欣賞。七八個小時後,他們到達芒市,郭姐又帶他們轉車,出了遮放,最後到達了邊境小鎮——芒海。
這裏有一條小河是中緬兩國的邊境線,對岸是緬甸木姐縣的勐古鎮,遠遠望去,一片祥和,卻只是表像而已——勐古鎮鄰近果敢,歷來是緬北地區各支武裝力量爭奪的地盤。吳二叔他們去的時候,緬甸政府已經取得了這裏的實際控制權,毒品交易雖然沒有90年代那麼猖獗,但還是大有人在。
第二天一大早,郭姐帶著他們三個來到一片甘蔗林,找到一條小路,她先鑽了進去。附近人煙稀少,吳二叔的心砰砰直跳,他明白,只要跟上去,就是一條不歸路。後來他告訴我:“當時除了緊張還是緊張,甘蔗葉劃到臉和手都不知道疼。”
快走到甘蔗林的盡頭,郭姐讓他們停下,她先把頭探出去看,沒發現巡邏隊伍,才示意他們跟上。不久之後他們來到河邊,這段河不寬,也不深,3個新手小夥站在河邊緊張得不行。
“放鬆點,巡邏隊過去了。我們站的地方是中國,過去就是緬甸,大財就在那裏等著。”郭姐率先跳下河提,水高還不到膝蓋,3個小夥子也跟著跳。吳二叔回頭看了一眼,一片甘蔗林隨風揺曳。

河對岸,勐古鎮的房子大多蓋著石棉瓦,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棟小樓房鶴立雞群,郭姐的老公大財已經等候多時了。
3.危險的甜頭
最早,郭姐夫婦在這一帶打零工、開早點鋪,後來見人幹這行發了財,索性跟著幹。三四年過去,他們有了“據點”,可以輕車熟路地帶人混過鎮上的關卡。
3個驚魂未定的小夥被帶到一個髒兮兮的小旅館,郭姐的老公到門口了一通電話,個把鐘頭後,有人用暗號敲了門。雙方對了幾句黑話,門開了,一個身材高大,膚色有點蠟黃、滿臉戾氣的男人拎著一個黑色袋子走了進來。
“三哥。”郭姐的老公趕緊打招呼。
三哥點點頭,看了幾人一眼:“就他們三個?”
郭姐說是,都是頭一次來。三哥這才和吳二叔他們打招呼,叫他們不要緊張,又堆起滿臉的橫肉,親熱地假笑: “我和你們一樣,也是中國人。”
三哥說完,打開黑色袋子,從裏面拿出3個裝著白色粉末的透明袋子。這些白粉就是“毒品之王”海洛因,一共900克。郭姐拿出一堆事先準備好的避孕套,和老公一起分裝,每個裏面裝8至10克,裏緊、紮牢,他們動作嫺熟,不一會兒就裝好了。
看到這堆東西,吳二叔瑟瑟發抖。
“來,吞下去。”三哥說話的語氣很瘆人。
3個小夥別無選擇,只能忍著噁心,戰戰兢棘地吞。吞下300克海洛因,吳二叔覺得自己只能聽天由命了。之後,三哥拍拍他們的肩膀,“祝你們好運。”
郭姐叮囑他們,“卸貨”之前,在途中只能少量喝水,吃一點水果保持體力,不能再吃其他東西了。進食會加快胃的蠕動,一旦包裝被胃液腐蝕,哪怕只洩露1克海洛因,都足以致命。 郭姐帶他們原路返回,偷渡回國,穿過了同一片甘蔗林,一來一去,吳二叔的心境變了。從芒海到芒市, 路上每過一道關卡,他都“怕得心都要跳出來了”,可表面上還要努力強裝鎮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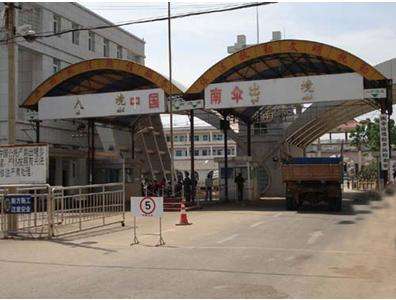
到達芒市,為了避免被警方一鍋端,郭姐讓3個小夥子分頭行動,去各自的目的地交貨。吳二叔去的那座城市沒有直達客車,要在半路歇一夜,他沒有手機,郭姐就讓他在某市的醫院門口買一瓶“李子園”拿在手上,說到時會有一個穿白色T恤、打傘的年輕男人與他接頭。
一路上,除了固定關卡,還有緝毒員警臨時檢查,吳二叔年輕,面相憨厚,並沒有引起員警太多的懷疑。就這樣,他成了一條漏網之魚。 到達目的地和接頭人匯合,對方確認沒人盯梢,又帶吳二叔繞了幾條街,去了一個巷子深處的小旅館。進了房間,還有一個男人從他背後關上了門,他給吳二叔吃了瀉藥,不多時吳二叔跑進衛生間,裏面有個盆。
後來,吳二叔跟我說,“噁心得很,不知道吸毒的人怎麼吸得進去。”
那個男人清點了海洛因的數量,就從錢夾裏拿出一疊百元大鈔,數出54張——5400元錢,吳二叔在修理廠幹一年都搞不來,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拿這麼多錢,手都抖了起來,抓著錢又數了一遍。
那個男人離開之前,叫吳二叔“不要虧待自己”,好好去放鬆一下,“去找個好一點的酒店住”。吳二叔照辦,第二天他坐車回到修理廠,一路上壓抑著內心的狂喜,心想再幹幾次,再幹幾次,就收手。
大筆的錢來路不正,吳二叔不敢張揚,他只敢慢慢地把抽的煙從2塊一包的春城換成5塊一包的紅河。他偶爾會請同事唱歌吃飯,大家都說他有錢、豪氣,這樣的恭維讓吳二叔很受用。慢慢地,他花錢就更大膽了。
在修理廠後面的三四個月,吳二叔幹活的時候,徹底沒了心思。他決定“再去一次”,不等郭姐來叫,他就主動找到郭姐,請她幫忙聯繫,他要單獨“走一趟”。

2002年春節,吳二叔回到家,購置了一身體面的行頭,抽的煙也更貴了。他還花了800多元買了一部諾基亞手機別在褲腰上,在寨子裏打電話,“哇啦哇啦”的。這副行頭和做派令村裏的幾個同齡人羡慕不已,他們問吳二叔做了什麼生意,吳二叔沒管住嘴,洩露了一點,有兩個傢伙揺揺頭表示自己不敢幹。不過,他們不久之後還是跟著上了道。
一個親戚提醒我姑婆說:“要注意一下這小子,修車搞不來這麼多錢,怕是搞了什麼壞事情。” 等家裏大人問起,吳二叔就說自己是在休息的時候去老街賭博、幫人賣電視賺來的。父母警示了一番,就被他忽悠過去了。
春節過後,吳二叔似乎已經“販毒成癮”,又去了一趟勐古。這一次,三哥開始有點賞識這個大膽的年輕人,就破例帶他去看制毒作坊。
他跟著三哥穿過一條小路,進了一間簡陋的石棉瓦房,三哥打開一間房門,裏面是空空如也,沒人,他走進去掀開地上的一塊破舊木板,一把通往地下室的梯子露了出來。
吳二叔跟著爬了下去,這間地下室並不大,裏面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瓶瓶罐罐,散發出刺鼻的氣味。吳二叔只認出了那堆黑色的東西是鴉片,還有幾桶是酒精,其他的藥水他從未見過。
地下室裏有五六個人正在幹活兒,其中有緬甸人,好像也有中國人,他們看到陌生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動作。三哥和其中一個用緬甸語說了幾句,他們又各自忙了起來。
吳二叔四處看,看不出什麼名堂,就跟三哥告辭,說自己是請假出來的,送完貨還要趕回去上班。三哥要留他住一夜,說幹這行的,腦売別在褲腰帶上,要好好享受當下。吳二叔想了想,覺得有道理。
從地下室出來,時間尚早,他倆就坐下來喝茶、聊天。三哥突然從口袋裏掏出一瓶麻黃素,遞了一片給吳二叔,吳二叔推辭了,他販毒,但自己不吸,擔心路上毒癮發作壞了事。三哥也不勉強,獨自享受了一番,接著就說起了自己的故事。
三哥以前是個牲口販子,老家在百十公里外,十多年前因犯了一粧案子被警方通緝,他一路逃到勐古再也沒敢回去,恰好遇到了這裏毒品最氾濫、猖獗的時期。不過他不敢帶毒入境,就幫毒販找人,從中拿點“介紹費”,慢慢地有了積蓄、人脈後,就出來自立門戶。
在異國他鄉逃亡,三哥有時候也會靠吸毒麻痹自己。不過他從不吸食自己的制毒作坊生產的海洛因,“勁太大”。
晚上,三哥又帶著吳二叔花天酒地一番,他說:“我看你人機靈,年紀輕輕比我當年膽子大多了。我告訴你們老闆,提拔你做中間人,以後不要再自己帶了,危險。”
4.發展下線
之前,吳二叔只接觸過郭姐,並不知道幕後的老闆是誰。那次他回來順利上交了毒品後,一個小弟模樣的男人對他說,“斌哥”要見他。隨後,吳二叔被引到一個飯局上。
斌哥40來歲,中等個子,看起來有些文弱,說話也不緊不慢的,很儒雅。他是內地的毒品供應商,也流竄全國組織人販毒。
見到吳二叔,他說三哥已經和自己打過招呼了,又說三哥看准的人應該沒錯。幾杯酒下肚,他承諾吳二叔每帶一個“夥伴”過去,除了三哥給的1500元的“介紹費”,他這邊還有分紅 ——每次20克海洛因。
就這樣,吳二叔從修理廠辭職了,他跟家裏人說自己要和朋友到芒市做水果生意,順便幫人賣賣電視。隔個把月,他就往家裏帶幾百塊錢,家人都覺得他聰明,找到了賺錢的門路。
吳二叔開始著手給別人介紹“生意”,鑒於自己被郭姐帶入這行的經歷,他也把目標對準那些沒讀幾年書就進入社會、愛玩、收入低的年輕人。
他的第一個下線是個老鄉,修車的時候認識的,對方沒有固定工作,看到吳二叔曰漸發達,主動找上門想跟著他“發財”。吳二叔本不想帶熟人去,但老鄉說不怕,“萬一進去也不會怪你”。吳二叔就答應了,在短期內取得陌生人的信任是件很難的事,就算別人有這個想法,也會懷疑他是“水鴨子”。
“水鴨子”有點像線人,又不是線人,他們誘惑別人去販毒,自己從中賺介紹費。如果對方只帶幾百克就算了,要是遇到膽子大的、敢帶幾公斤幾十公斤的“大魚”,他們就會向警方舉報,黑白通吃。
尋摸了一段時間,沒有陌生人上鉤,吳二叔只好把目標對準過年回家遇到的那兩個夥伴,這一次遊說,他們沒能經得住誘惑。
2002年年中,吳二叔帶著3個老鄉去勐古的小旅館拿東西。三哥給了他4500元“介紹費”,
斌哥讓他“入股” 20克海洛因。這次他拿到手5000多元,和自己帶貨差不多,但風險陡降。
過了幾個月,芒海風聲緊,查得嚴,吳二叔只好帶3個“老手”去棒賽,準備從畹町口岸偷渡。可是在前往棒賽的路上,他們遇到了一支隊伍,十幾個人背著槍,要看他們的身份證和相關的出境證明。
十幾把槍栓“曄啦”一響,吳二叔和同伴的腦袋都被槍指著,他們心想自己這次算是完了。萬幸的是帶路人會講緬甸語,交涉一番,對方讓他們拿出8000元錢就算了。
帶路的人翻譯說:“如果不拿,那就沒辦法了,只能送你們幾個進監獄。”
這次經歷之後,吳二叔體會到了真切的恐懼,開始失眠。2003年,他聽道上的人說風聲緊要小心行動,就開始經常做些莫名其妙的噩夢了,於是決定先“歇一段時間”。 那時我才讀六年級,即便吳二叔在家,我倆也很少見面。5月左右,吳二叔和幾個親戚在幫山下的一戶人家砌山牆,工錢20元一天,當時算是不錯的。我聽大人說,他回家幹活兒是因為 “外頭的生意不好做了”。
5.背叛
一天晚上,吳二叔收工回家,修理廠的前工友阿寬突然找到他家裏,面色優鬱,欲言又止。吳二叔知道肯定不是什麼好事,就把他帶到外面。
阿寬哭喪著臉說,不久前他和別人打架,把對方打傷住院,法院判他賠16000元,“把我賣了也不值這麼多錢啊”。
吳二叔說自己沒錢借,阿寬連忙解釋,說自己是想跟著吳二叔去賺點大錢。吳二叔大吃一驚, 看了看周圍:“狗日的你亂說什麼?你再亂說我打死你信不信?”
阿寬說,自己一直都知道吳二叔在幹什麼,但從沒跟別人說過,這次是實在沒辦法了才來求他。阿寬說完低下頭,模樣很可憐,吳二叔也低頭看了看自己手上因為幹活磨出來的血泡和老繭,又心動了。
因為阿寬急需用錢,吳二叔來不及找其他人同行,第二天他們就匆匆上路。路上,他告訴阿寬,自己帶3個人才劃得來,最近風聲緊,查得又嚴,“帶你出來完全是出於義氣”。吳二叔一再叮囑:“萬一被抓了,不要把我供出來。”
阿寬讓他放心,信誓旦旦地說,“我們倆什麼關係,怎麼可能會把你供出來?就算被槍斃了都不會。”
這一次,求財心切的阿寬在勐古吞下了將近400克海洛因。吳二叔把他帶回芒市送上路,又回家繼續幹活,等待這陣風過去。
2003年冬天,阿寬出事了。第一次販毒成功後,他賺快錢上了癮,後來又幹了幾次,最後在 某縣城交貨時被員警當場抓住,人贓俱獲。
斌哥打電話過來,提醒吳二叔小心一點。吳二叔說自己好久沒幹了,“阿寬是我朋友,他不會出賣我的,沒事”。斌哥又說,這陣子好多人被抓,他感覺有點不踏實,“我們不要再聯繫了”,然後掛了電話。
快要過年了,天也冷了,寨子的路邊零零散散放起了鞭炮,是那些外出幹副業的人陸續回家 了。吳二叔老老實實在家幹活,哪里也不去。可這時候,某縣公安局緝毒大隊已經從阿寬嘴裏 掌握了吳二叔這幾年的犯罪情況,鄉派出所的民警也開始暗地調查吳二叔的行蹤。
年底,一輛警車趁著夜色悄悄駛入我們寨子,4個帶槍的員警封鎖了進出寨子的南北通道,吳二叔輕輕鬆松就被制服帶走了。姑婆哭哭啼啼的,每天以淚洗面,有人出主意,讓他們趕緊找律師,爭取把人從看守所裏撈出來,至少能減點刑。

律師對撈出吳二叔有一定的信心,因為他只是被人指控,被抓的時候身上並沒有帶東西,“除非他自己鬆口承認,否則警方無法定他的罪。”律師表示,給3萬塊錢,他就能去“活動”, 如果把人撈出來了,他就收錢,如果撈不出來就全額退款。
大家都覺得這方案不錯,可吳二叔的父親、我的姑公說:“自作孽不可活,就讓法律來懲罰 他。我們管不了他就讓監獄來管,別說是3萬,3千都沒有!”
姑公讀過書,是寨子裏的文化人,非常好面子。兒子被抓令他非常憤怒,覺得是家門恥辱。
姑公早先學習爆破,拿到證書之後在砂石廠上班。幾年後,年近花甲的他又承包了一個石場,自己經營。我去過那個採石場一次,在一條河邊,遠離人煙。有兩間空心磚和石棉瓦搭起來的小房 子,一間是廚房,一間是宿舍,裏面只有一張木板搭起來的床。
姑公對我說:“我也是命苦啦,這麼大年紀還要出來碰命(方言,拼命)。我還是知道點苗頭的,我一直告訴你二叔不要妄想著發大財,他聽不進去。”
沒過幾年,應環保部門的要求,姑公的石場關停了,可租用挖掘機等設備、貸款的利息錢都沒賺回來。姑公沒辦法,又跟著別人去工地打工,他先後到過安徽、新疆……幹過建築、種植等行業,哪里賺的多就去哪里,什麼髒活累活都肯幹。
如今,姑公已經六十多歲,還在外省漂泊。欠下的債還沒有還清,哪里來的3萬塊。
6.認罪
吳二叔被抓的那天晚上,他的心不太慌,他在斌哥那裏學到了一些法律知識,知道只要自己不鬆口,員警拿他沒辦法。
提審,一個晚上下來,負責審問的員警羅列了他的種種罪行,但吳二叔一口咬定自己沒做過。 第二天早上,他也只承認自己帶阿寬販過毒,之前的事,依然不認,還罵道:“這個小雜種, 怎麼這樣誣陷人!”
下午,警方改變了審問策略。一個年紀大的員警開始表揚吳二叔,說他口風把得緊,心理素質好,不像大多數毒販,一句“坦白從寬、抗拒從嚴”,就什麼都交代了。
吳二叔感到很受用,員警又說他還有做“線人”的潛質,問他願不願意。吳二叔心裏來了勁, 覺得如果做了警方的線人,他就能黑白兩道走,“豈不是能在這條路上大有可為?”
他招供了,並且在口供上簽了字。
吳二叔被關進了看守所,衣服、褲子上的紐扣、拉鎖,凡是有可能造成傷害的銳器都被一一剪除。直到冷水從頭澆下來,吳二叔才從做線人的白曰夢中醒來。
那個長方形的監房裏已經關了七八個犯罪嫌疑人,都不懷好意地打量著吳二叔。簡單盤問後, 他們要按慣例給新人“開小庭”。4個“打手”站在兩邊,“老大”坐在中間,老大問吳二叔犯了什麼罪,聽完之後決定打他3拳。他們選定地方,讓吳二叔背靠牆,打手們排著隊,輪流上場。第一個人用力打了吳二叔胸口一拳,第二個上來打肚子,吳二叔疼痛難忍,等第三個人過來時,吳二叔趁他不注意,雙手掐住他的脖子,用膝蓋頂他的下盤。那人吃痛,滾在地上叫哭爹叫娘。
員警懲罰了吳二叔,之後給他戴了腳鐐,換了一個監房。在這裏,吳二叔竟然遇見了自己的老闆斌哥。
斌哥有錢,所以在這個監房裏當上了 “老大”。吳二叔說完自己的事,斌哥就故意嗆他:“你還說是那個小雜種是你的朋友,這麼快就栽在他手上了?”接著斌哥又問吳二叔,為什麼不把他供出來立功,“我都在裏面了,有可能完蛋了”
吳二叔沒有說話。
斌哥是被手底下的一個小弟供出來的,被抓的那天,他正在賓館裏睡覺,小弟帶著員警破門而入,給他戴上手銬,把搜到的毒品往脖子上一掛,就拍照取證了。
斌哥對吳二叔說:“幹我們這行沒有朋友”
7.“給你1萬塊。”
在看守所關了7個月,到了2004年夏天,法院開庭審判吳二叔的案子。因為合謀他人走私販賣毒品,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。
這處罰算輕的了,但吳二叔不服,覺得自己只是個小嘍啰,提出上訴。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,維持原判。判決書下來,吳二叔徹底死了心,那年他21歲,之後的15年,剛好是他人生中最好的年華。

因為在監獄裏表現優秀,吳二叔在2012年夏季被提前釋放。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,是個大清早,家人還沒到。吳二叔在監獄附近繞了一圏,呼吸著自由的空氣。他告訴我:“如果有文化的話,我當時想寫首詩,可惜一個字也憋不出來。”
再繞回到監獄門口,家人已經在那裏等候了。那天晚上,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,吳二叔發現自己根本夾不起菜,在監獄裏待了8年,他一直都是用勺子吃飯,都快忘記如何使用筷子了。
8年時間過去,日寸代變了,街上的車多了,各種品牌的智能手機讓人看花了眼,就連寨子裏的 平頂房都起了好幾棟,土路也都完成了硬化。
吳二叔不想打聽之前身邊人的下落,享受了一段自由的生活後,就踏踏實實進了一家水泥廠做臨時工。不過工資實在太低了,吳二叔感到很害怕,他怕自己又經受不住金錢的誘惑,於是決定出去打工,離邊境遠遠的。
其實從2010年開始,到沿海打工,似乎已經成為我們寨子裏的大多數人的謀生選擇。三五成群在路上閑遊的人少了,去緬甸幹副業的人少了,冒風險去販毒的人就更少聽說了。
聽一個在外打工的親戚說,吳二叔到了工地後,能加夜班就加夜班,200塊錢一天也幹得很拼命。一年下來,他把在監獄裏養起來的肥肉都掉完了,我過年回家看到吳二叔,他又恢復到以 前瘦削的樣子,皮膚曬得黑紅黑紅的。
2018年,吳二叔跳槽找到了一份新工作——氬弧焊,專門焊接品牌店裏的大衣架。他聰明, 技術學得快,又喜歡鑽研。那段時間,他經常和我打電話,津津有味地講怎麼焊,花紋才好看。我聽不懂,他又說起一件趣事,廠裏的老闆問他要多少錢一個月?他不敢多說,要了8000塊,覺得已經夠多了。可最後老闆笑了笑:“給你1萬塊。”
